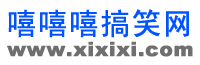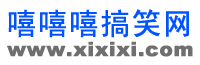要赏识“幽默”也真难。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。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,就不必这么大,脚底要小得多,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?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,肉也用不着这么多。那么,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。有时告诉人们,大抵以为是“幽默”。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,或自己遭了打,我想,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。
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,是在尽先输入名词,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。
于是各各以意为之。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,便称之为表现主义;多讲别人,是写实主义;见女郎小腿肚作诗,是浪漫主义;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,是古典主义;天上掉下一颗头,头上站着一头牛,爱呀,海中央的青霹雳呀……是未来主义……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: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,无可质证,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匾额。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。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,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,争执起来了,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。又无可质证,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。那人望了一望,回答道:“什么也没有。匾还没有挂哩。”
我想,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,也总得先有那块匾额挂起来才行。空空洞洞的争,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。
·上一篇文章:
教 书
·下一篇文章:
中国文人的俏皮话